火瀑游戏故事背景 官方小说
第八日、战场日志2
以下内容为European Union fleet Lieutenant Commander,Orestes Nostromo在Crystite Wars 期间任F-85 Remora驾驶员的证词。这段证词是Crystite Wars结束后由一名新闻记者所记录。
Aris Holden–历史学家
我记得我在雅典的童年片段,那是在Firefall降临之前。虽然这些记忆已成往事。我记得我的木器,我记得她带我去利卡贝托山的帕台农,赫菲斯托斯神庙。她想让我看看先祖们的杰作。我记得我爸爸总带我去奥林匹克体育场看老式足球比赛。
我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古雅典时代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和我父亲在伦敦度假时,Firefall恰好发生,这对我的家族是一种多么悲剧的打击。然后随着War of Reunification和Ivan对希腊的入侵(Ivan是EU部队在Crystite Wars期间用于侮辱俄罗斯军队的词),你可以想象我和我父亲的感受,我们的家永远不在了。
我想就是从那时候开始,我对Ivan的仇恨开始积蓄。从那天开始,我一天天地数着日子过,直到我18岁成年。我立刻申请加入EU军队,期望有一天能解放希腊。
当然,Crystite Wars给予了我机会。我参加了雅典之战。
那时候我是E.U.S. Morningstar的歼击机驾驶员。歼击机就和20世纪护卫轰炸机的僚机一样。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护送的是一颗疯狂的炸弹,而我们却在它下方几千米处执行护卫。炸弹会从一万公里的轨道直捣地面。
在雅典期间,我驾驶的是F-85 Remora。这是一种安逸的小型双人战斗机,配备有加强热能护盾和中级炮塔。作为歼击机它再好不过了。我的机枪手是Ulmer McTish,一个暴躁的爱尔兰小个子,枪法神准。他是一个好人,一个好的副手。
我们护送的炸弹目标是雅典中心的一处Ivan导弹能源厂,我们的任务是保护炸弹不被导弹击落。我们是进攻的第一纵队,如果我们没能炸毁能圆场,陆战队员们就会在着陆前被活活打死。
Morningstar在我们从港湾发动进攻前就已经遭受攻击。这是通往大气层外一万公里的路程,我们的护送之旅弹火满天。Ulmer干的很好,赶走了很多来犯者,我也干掉了几个。我们的僚机,Briggs,做的比我们更好。
我们坚持到了盲降区,炸弹仍然没有偏离目标线路。盲降区是当你抵达大气层,电浆的爆炸会亮如白昼,让你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们冲出了盲降区,但真正的混乱才刚刚开始。
我们发现我们正置身于防空火力之下,Pav-90 Valkyries、反导导弹,甚至还有空雷。我们只剩下一分钟了,但是这一分钟过的好像一个小时。我们就好像打完就可以回家一样疯狂地倾泻着炮火。Ulmer在观察任何飞向我们两翼的导弹,Briggs和我只管杀出一条血路。
当炸弹接近目标后,我在10G的位置放下了炸弹。通过无线电我告诉Brigg进行核准。但是(Nostromo说到这里,脸上十分的沮丧)
一般当炸弹抵达后,你通常都会置身于敌区的中心,歼击机的任务此时就立刻变成火力全开,并准备逃至友方领空。我们的指挥官说,"如果你们还有弹药,就给我打光了再回来。"
于是Ulmer和我就与Ivan Valkyries展开了激战。
我们交手了几次,我击落了4家敌机,差点破了记录。Ulmer击落的则更多。雅典之战曾发生在神话中,这让我想起了关于Clash of the Titans的传说。那真是天启般的场景。
当我们的弹药打光后,我调头朝我们的掩护部队飞去。常规来说它会带我们从帕先农神庙上空飞过。我想看看那神庙,这么多年了,你明白我的心情。当我们飞过时,我看到的只是一片瓦砾。一架Ivan Valkyrie把它砸了个粉碎。
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形容,不过有时候我会想,那架敌机也许正是被我击落的,这让我心存恐惧。
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,雅典之战随着希腊的解放而结束。一年后,当我得暇休假时,我回到了雅典,又见到了家乡的城市。
但是所有我曾与父母踏足的地方,唯一还留在那里的只有利卡贝特山。其余的一切都在解放过程中被摧毁。只过了几天,我就离开了雅典,提早回营述职。
记忆中的家园已经不在,我踏足的已然并非故土。
-你和你母亲还有家人最后团聚了嘛?
在那次旅行中,我回到了我童年的住处……
[Nostromo 停顿了一下]
或者说,活在我记忆中的住处。
更多相关资讯请关注:火瀑专区
- 标签:
- 背景故事
-
22日《火瀑》国服正式开启风暴测试,此次测试除了过往的内容之外还曝光了最新幽灵战甲视频,一起来看看。2015-09-22 11:09:020
-
期盼已久的视觉盛宴,将在今日14点准时开启,《火瀑》(Firefall)将在今日让好莱坞硬科幻风暴再次席卷大陆!2015-09-01 09:09:180
-
距离好莱坞硬科幻网游《火瀑》9月1日先锋测试开启时间还有5天,只要加入游民星空《火瀑》官方群,100%拿激活码!2015-08-27 17:08:410
-
好莱坞硬科幻网游《火瀑》(Firefall)生化战甲视频首曝,可火力支援亦可为友军疗伤,他们是医师、药剂师、战士的结合体,天生的医药天才!2015-08-26 23:08:400
-
好莱坞硬科幻网游《火瀑》(Firefall)无畏战甲视频首曝,重机枪火力清扫、超强悍的防御能力,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的气势在横扫千军的那一刻显露无疑!2015-08-26 23:08:190
-
好莱坞硬科幻网游《火瀑》登陆中国,硬科幻风暴席卷大陆,先锋测试将于9月1日拉开帷幕,激活码发放活动今日开启。2015-08-24 11:08:090
-
火瀑摩托车任务怎么做?火瀑摩托车限时任务并不难,只要熟悉路况就会像视频里一样狂飙起来,不熟悉路况的人请看红摩托限时任务视频演示。2015-08-14 23:08:080
-
火瀑PVP打法,看到最后的一人一定会笑,在PVP场里猥琐才是王道,要是飞到高处的空中会怎样呢?下面来看小编为大家带来的PVP视频演示。2015-08-14 22:08:460
-
火瀑新手怎么玩?火瀑游戏内的任务引导十分准确,很容易上手,趁着没公测小编给大家带来一个火瀑教学视频,半小时以后你就是高手了!2015-08-14 22:08:290
-
火瀑美服公测大改版,看着遥遥无期的国服,再加上创作团队的主要人员辞职,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晚上,抛开这些,先来看看火瀑优秀的内容吧。2015-08-14 21:08:580
-
厌倦了站桩“突突突”的射击游戏?现游民星空《火瀑》抢码通道已全面开放,来就送激活码,绝对零门槛!2015-09-18 17:09:160
-
期盼已久的视觉盛宴,将在今日14点准时开启,《火瀑》(Firefall)将在今日让好莱坞硬科幻风暴再次席卷大陆!2015-09-01 09:09:180
-
距离好莱坞硬科幻网游《火瀑》9月1日先锋测试开启时间还有5天,只要加入游民星空《火瀑》官方群,100%拿激活码!2015-08-27 17:08:410
-
好莱坞硬科幻网游《火瀑》登陆中国,硬科幻风暴席卷大陆,先锋测试将于9月1日拉开帷幕,激活码发放活动今日开启。2015-08-24 11:08:090
-
《火瀑》是一款动态的开放世界MMO射击游戏,故事发生在2177年的未来地球,由于一场行星撞击的“火瀑”事件,地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。2015-08-22 14:08:090
-
火瀑原画集欣赏。火瀑游戏官方原画欣赏,各位喜欢火瀑游戏的看官们可不容错过哦。2015-08-21 18:08:470
-
火瀑角色属性机制。横向角色发展并不是为玩家角色人物增加更多的生命值、伤害值或者自身抗性质,而是为玩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,让他在面对更强大的敌人时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。2015-08-18 20:08:480
-
究竟何日开始公测目前我们并不知晓,不过在公测之前,小编已经通过独家渠道获取了《火瀑》中文版本部分游戏截图,让我们一起先睹为快吧。2015-08-14 16:08:270
-
火瀑评价怎么样?火瀑从落户中国的那一刻开始就受到玩家们的广泛关注。最近火瀑又有了新的动作,游戏官网超首页全面升级,并将于近日正式上线。2015-08-14 11:08:400
-
耗时七年开发,傲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代理运营的好莱坞级硬科幻网游《Firefall》,今日正式确定中文名为《火瀑》。2015-06-29 14:06:410
-
 火瀑美服公测真人预告片完整版 电影要来了
火瀑美服公测真人预告片完整版 电影要来了
 好莱坞硬科幻网游火瀑 开发者视频曝光
好莱坞硬科幻网游火瀑 开发者视频曝光
-
 卡通渲染高质量大作火瀑 Red5访谈视频(下)
卡通渲染高质量大作火瀑 Red5访谈视频(下)
 PVP试玩演示视频 决斗新地图SunkenHarbor
PVP试玩演示视频 决斗新地图SunkenHarbor
-
 玩家自制视频风景独好 度假圣城Copacabana
玩家自制视频风景独好 度假圣城Copacabana
 玩家在二测时录下的记录影像 供大家鉴赏
玩家在二测时录下的记录影像 供大家鉴赏
- 1
- 2
- 3
- 4
- 5
- 6
- 7
- 8
- 9
- 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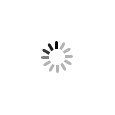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硬科幻网游《火瀑》工程战甲视频首曝
硬科幻网游《火瀑》工程战甲视频首曝 《火瀑》各职业高端装备亮相——奥姆达-M篇
《火瀑》各职业高端装备亮相——奥姆达-M篇 策略至上 《火瀑》带你走进战术射击世界
策略至上 《火瀑》带你走进战术射击世界 爆乳美腿蕾丝边 妩媚性感浪无边请快快点我
爆乳美腿蕾丝边 妩媚性感浪无边请快快点我 社区活动和猛犸象王之怒 一大波高清图来袭
社区活动和猛犸象王之怒 一大波高清图来袭 游戏人设开发设计图 3D动漫风格一样复杂
游戏人设开发设计图 3D动漫风格一样复杂 好莱坞式的硬科幻枪战网游火瀑试玩截图欣赏
好莱坞式的硬科幻枪战网游火瀑试玩截图欣赏 火瀑评测由表及里皆受好评 保有经典MMO风格
火瀑评测由表及里皆受好评 保有经典MMO风格 火瀑神秘货柜抵沪 好莱坞模特轮番试镜
火瀑神秘货柜抵沪 好莱坞模特轮番试镜